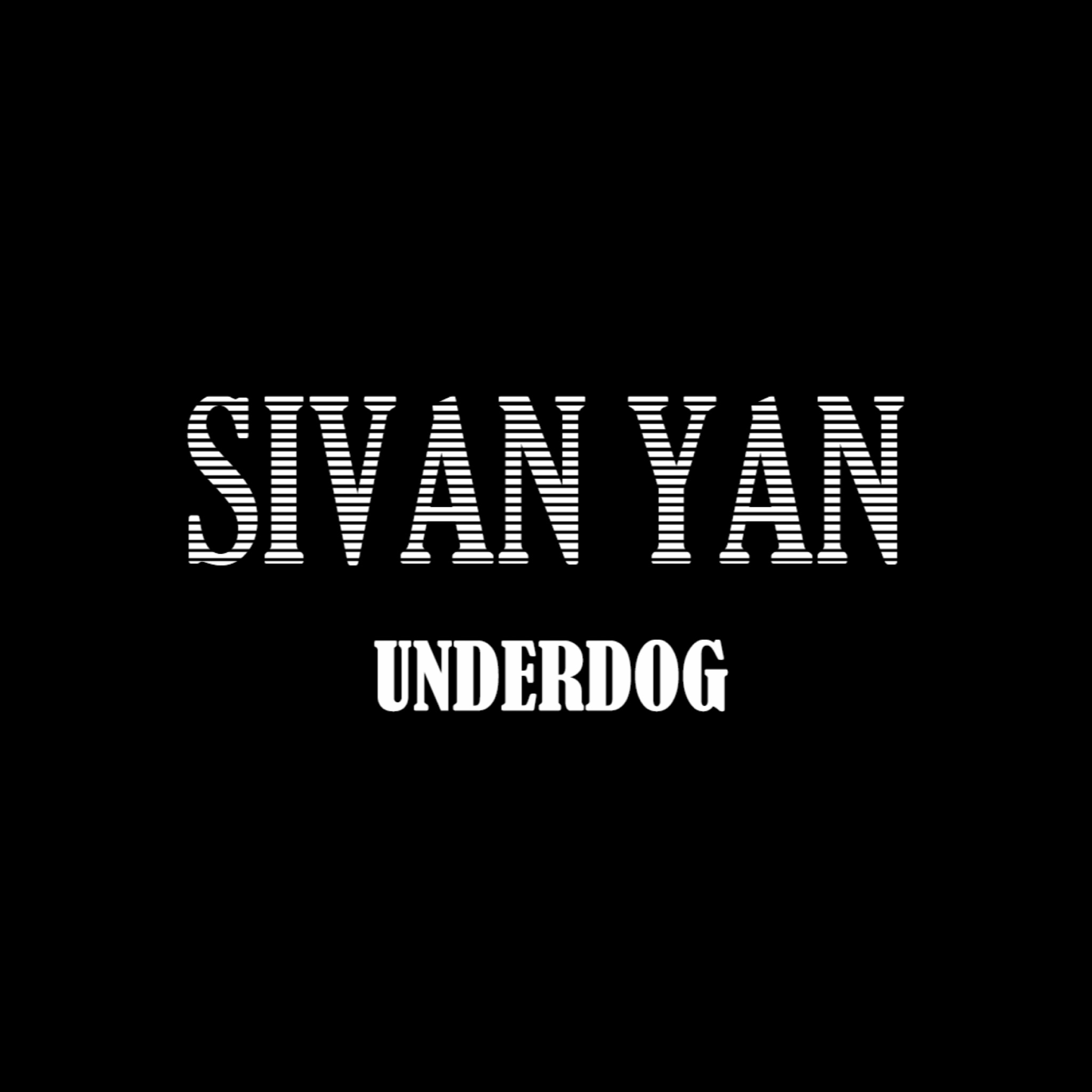三月份的湖南夹杂着闷热和湿的雨天,被子上的潮湿像不懂事一样,能挤出些许水分。我每周必做的事,就是在两个城市间来回切换。列车一共停留八次,你能看到城市三环的工业区,二手车售卖停车场,垃圾集中站,偏僻的学院,废旧的仓库,连锁的Outlets,很多不起眼的山,和一些在铁路延边的村庄。以及在铁轨旁穿插的高架桥,国道,零散的行人。
湿润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,只是会偷偷储藏起来,像盛放的容器,不经意在若干年后被动的打开,你能看到浑浊的记忆在旋转的过程。我已经厌倦了平常的事物,让人提不上劲的午后,连思维也变得迟钝,情绪像流动在毛细血管里的血液,铺满全身的同时让人窒息。按下快门的想法也感到不合时宜。
这多么像现在的摄影术,在新客观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权威的时代下,wolfgang timans们持续创造出一些相似而似是而非的东西,对于观念摄影的解构,影像创作的底色就像闷热天气里的那份潮湿,通过穿越不同时代推崇的影像主流文化之间,从Stephen Shore到alec soth的迭代里,人们不断为影像赋予所谓的意义,挖掘深层次的价值,持续填充比以前更饱满的“表达欲”,试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可是不同身份的变换会被迫带来的共情能力所及的局限,对于摄影术植入的记忆里,有多少是单纯寄生于某种设定的叙事下,强加并充满在条条框框的意义里。对于内容的陈腔滥调,照片包含的信息被过于映射主题的对象所失真挪用。而当初的原始感情,单纯的美学情感似乎如同廊桥遗梦般被我们丢失在了昨天。
做一些直觉般的,纯粹而直观的影像大概是我一直维持的状态。从某种意义上,摄影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,而是立体的,而我正在尝试向后转动,给出形而上的答案,如同桑格对待相机下的人们,他们的表情中没有侵入感,奥古斯特只是通过相机的历史时态讲述他们不同的故事,通透而不带有个人歧见的肖像,没有抗拒与扭曲。其发展的实践方式需要脱离超概念且大而无物的语境中,而平实的语言才会放射一些共同的记忆与情感。
好像回到了人们误解摄影术的年代一般。回望那些过时的银盐相片,他们永远不做审判,总是让心如摄取灵魂般滴血,却永不夸大。两个世纪走过,没人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。作为结尾,我想引用一些卡蒂埃-布列松的话。
“抓住各种巧合,我们才可以瞥到在内的秩序…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难以忍受,它比19世纪更糟。19世纪结束后直到1955年,在此之前,还有希望…”